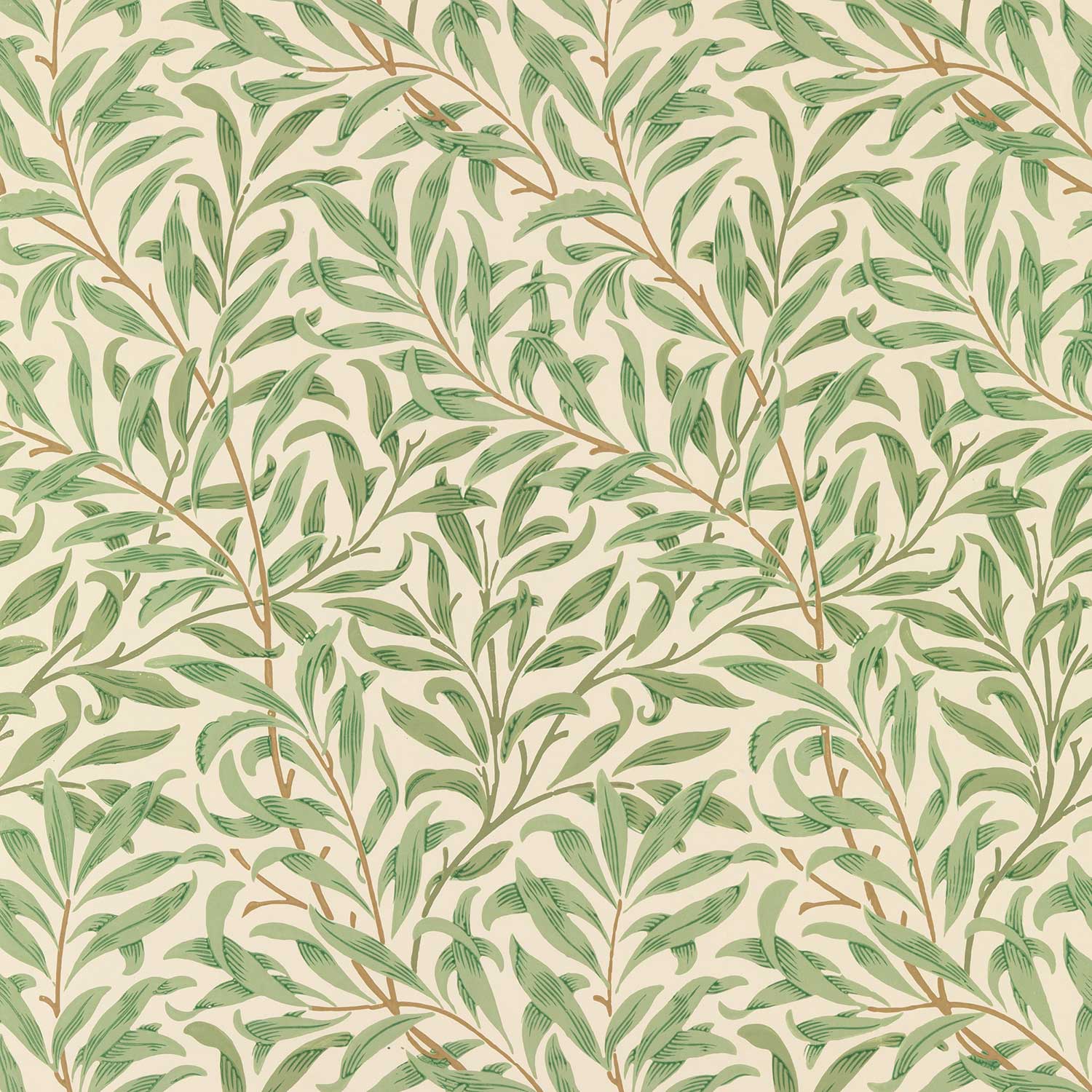type
Post
status
Published
date
Jan 25, 2025
slug
poet
summary
探讨屈原、曹丕和陶渊明的作品,分析他们对时间、死亡和人类存在的思考,强调在历史变迁中个人的感受与选择,以及在自然与生命中寻找意义的过程。
tags
文字
推荐
category
心情随笔
icon
password
第一讲 屈原:时间的焦虑
01 土拨鼠变鹌鹑,老鹰变斑鸠的“环形时间”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我们都存在。”
提出:“时间迷宫”的观念 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个将来。
打破了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建立了一种网状的时间观
博尔赫斯认为时间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面对时间,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不同的焦虑感。
- 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在两个时代的交界之处,常常会产生第一流的作者。那是因为他们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多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到来和新观念的冲击。而屈原就是一个这样的作者。
- 像他们这样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往往会难以理解。那是因为对于和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不大能够同样程度地感到新时代带来的震撼。而对于他们后代的阐释者来说,他们又很难理解古代的生存状况。
从“时间的焦虑”这个角度来讲解屈原《楚辞》《九歌》《离骚》
屈原的时代背景:
屈原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基本上进入理性时代了,而楚地依然还处于神话时代之中。楚地的这种神秘性其实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依然都还存在。
当时楚国的这种神秘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巫和史是不分家的。我们知道,在上古的时候,巫和史使他们做不同的事情。巫师主管鬼神祭祀和宗教礼仪,而史官主管国家事务和氏族传承。可是在楚国,巫和史二者不分。而根据现在的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当时在楚国来承担巫史责任的那个官职就是三闾大夫,而三闾大夫正是屈原的官职。
因为屈原他同时要处理巫的事务和史的事务,所以他相当于同时要处理三个系统,就是神话系统、历史系统和现实系统。它带来的问题就是,他在处理这三个系统的过程中间遇到了巨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可以说,屈原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
屈原他所掌握的那么多的知识,也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离骚》中会看到那么多的草木之名,看到那么多的历史、神话的人名。那都是和屈原在当时他所在的社会中间,他对于知识的一种几乎是垄断性的掌握是有关系的。
可是,这样一种巨大的知识的掌握也给屈原带来了一个问题——当他在处理各种信息系统中遇到冲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楚国的第一个精神流亡者。
屈原也被自己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时间观念产生
神话时代的伊甸园是什么样子的?神话时代是人类第一个文明时代。在神话时代之前,人类还只是动物。
随着人类由猿变人,人们越来越多地掌握了知识,人们越来越多地进行自然的观察。时间这种概念就慢慢地在人类的头脑中间产生出来。
古代人的时间观念:一种非常原始而不准确的观察(以吃掉的土拨鼠数量来观察“时间”的变化→吃掉100只土拨鼠,我的牙齿就开始松动)
这样的一种观念它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懂得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产生了时间的焦虑。
如何来应付时间的焦虑呢?
“环形的时间观”
- 人们发现了自然节律。
《礼记·月令》:
季春之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
季夏之月......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在这四段里面说:在季春之月,田鼠就会化为鴽,鴽就是鹌鹑。然后在季夏之月,腐草就会变成萤火。然后到季秋之月,爵,爵就是黄雀,黄雀跳进水里面,它就变成了河蚌。然后到孟冬之月,雉,雉就是野鸡,它们也跳进了水里面,变成了河蚌。
古代的人通过这样一种非常不准确的自然观察,他们反倒产生了一种很能够安慰自己的观念,就是他们发现春夏秋冬四季流转,田鼠、鹌鹑变来变去,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这样的一种循环之中。
- 既然草枯黄了还能够再绿,田鼠变成鹌鹑之后还能够再变回来,那我们在大概生活了31年的时候死去,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大概会有另外的一种形式循环回来的。
画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楚帛书》
在这个书的周围是12个月神,循环往复的12个月神;然后在四个角上都是植物,所以它代表了一种楚人的观念,就是12个月循环往复,这些植物也是这样,草枯、草荣,然后又枯又荣,这样循环不停。
根据李学勤先生考证,楚帛书周围的12个月神的名目跟周人的书《尔雅》中间的12个月的名字是一样的。根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楚帛书的时间是公元前350年。可是我们现在一般不用考证,因为这个时间说得太准确了,我们现在一般说它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前400年。
屈原出生的时间就是公元前350年。我们可以把楚帛书看做是屈原所在的那个时间的一种时间观的说明。
如果我们生活的时间真的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环形时间,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按照时间来确定好了。一切按照时间确定好,意味着我们所有额外的努力都是不需要的。
线形时间观产生
在公元前350年的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我们会在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看到,民间还使用这种环形的时间观;可是在王公大臣的阶层里面,一种新的时间观成为了主流,这个新的时间观就是历史时间观。
这样的一种变化,它最重要的证据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儒家思想中的,比如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要去讲那些鬼神之事。还有一个证据是,中原记录历史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史官,而史官的记录更多地集中在内政外交上,而不是鬼神之事上。
可是人类就是这样子,你一旦把记录的注意力放在了人类社会的事实上,环形时间观就会破产。因为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的事实就是,离我们越远的事物与我们现在的差别就越大。
因此,在中原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中间,人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时间是线性.
《诗经》
主要讲农事的时候,它还是使用环形时间,以《诗经》的《七月》为代表。可是当它在记录社会历史的时候,它就是使用线性时间,以《诗经》中间的《殷武》和《长发》为代表。
在世界文学中间,环形时间基本上都更多地出现在神话中间,而且它一般都意味着和谐、安宁、有序。
线性时间其实是从史诗开始的。而且我们会看到,随着时间往下走,线性时间常常后来会走到一个很悲哀的结尾。所以我们甚至在世界文学中间会看到很多对于历史时间的憎恶。
《桃花源记》 英国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一个完全置身于历史时间之外的一个地方
托尔·金《魔戒》
把故事放在环形时间失落之后的那个破破烂烂的中土世界。
中土世界原先是很好的,但是环形时间失落了之后,它就变得不好了,它就变成了一片弃土。
- 为什么是屈原写出来了《离骚》,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中原的作者?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中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群体——诸子百家,他们通过系统性的思考,来群体地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屈原他因为生活在神话时代的楚地,所以他变成了一个独立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人。
02 生活在时代门槛上的屈原
《九歌》 神话时间的失落(环形时间的失落)
你看《九歌》里面的神都是什么样的神?都是失败的神。而《九歌》中间的失败的神,他们的失败常常就表现在时间的错位上。所以湘君等湘夫人,湘夫人不来,湘夫人等湘君,湘君不来。山鬼等他的情人,他的情人又错过了。在《国殇》里面,那些很年轻的、还不应该死的那些孩子,他们都去世了。所以《九歌》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时间的错乱和失序。
台湾的现代舞集——云门舞集,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九歌》,用《九歌》来表达现代人的忧伤。
我认为《九歌》它不是一个神秘主义的作品,而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作品。它记录的就是在神话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人对于过去的那种追念和忧伤。
《离骚》也是来讲历史时间对神话时间的打破,只不过它的表述比《九歌》要更加复杂。
香草美人的解读
《离骚》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叫作“众芳芜秽”。而在《离骚》的“众芳芜秽”的特点之上所产生的一种最重要的诗学传统,就叫做“美人香草”。
那“众芳芜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去看《离骚》的前三分之一,你发现屈原不停地在讲,这个花又凋落了,那个草又凋落了。《离骚》中间有大量的草木,它们的结果全部都是凋落,这就叫做众芳芜秽。
美人香草来自于汉代的王逸,他在《离骚经序》里面讲的这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说我们要把《离骚》看做一个寓言。王逸认为,所以你不要把《离骚》看作是一个真的去寻求美女的故事。你要把《离骚》看做一个借着这些对于花草的凋落、对于美人迟暮的怜惜,来讲一个人的个人生命失落、一个人的个人政治追求失败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王逸这样来解释《离骚》之后,《离骚》的主旨就变得跟儒家的经典差不多。所以《离骚》就可以被称为“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名字叫作《离骚经序》,它把《离骚》纳入了儒家的阐释传统。
典型例子:陈子昂《感遇》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所有的人去读中文系,老师都会说,这首诗它表面上是在说兰花,但是事实上是在说陈子昂自己在政治追求中遇到的挫折,以及是他感到自己生命落空的伤感。
这是美人香草之说带来的好处。可是美人香草之说它也会带来一些坏处。坏处是什么?当后代的阐释者,有时候他们是出于要教化民众的需求,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想提高某一个诗人或者某一种文学体式的价值,他们就把这些原先不一定有政治寄托的作品,把它说成有政治寄托。
这样的解读它其实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带来对于艺术的窄化。所以它也是政治对于艺术的一种吞噬。
反抗“香草美人”:
其实在古代,因为“美人香草”之说的经典,所以古时候的人他们并不直接来对抗这种说法。可是他们也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达他们对于《离骚》的不同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杜牧。
当杜牧读到李贺的诗的时候,他觉得李贺的诗非常地瑰丽、神奇,里面有各种奇幻的想象力。然后杜牧就说李贺的诗是《离骚》的真正的后裔。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人香草之说,只不过他们不直接说。
时间性的解读
《离骚》很长,很少有人把它全部读完,因为我们在读的过程中间会遇到大量的障碍。可是我们看《离骚》开篇的前十句,在前十句里面屈原就写到了一切的枯萎、一切的凋落,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第一句是一种历史时间,所以它是屈原在讲我的祖先是谁,我的父亲是谁。他想讲一个线性的秩序。
第二句其实讲的是一个神话逻辑,因为第二句“摄提贞于孟陬兮”它讲的是一种特殊的天象,“摄提贞于孟陬”这样的天象发生,和“庚寅吾以降”加起来就是屈原出生的那个时间,是寅年寅月寅日。而寅年寅月寅日这个时间出现的概率是60年一次,所以屈原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
第四句是讲屈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现代的人给孩子起名,名字取决于父母想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希望。那是因为现代人被假定生来没有特殊的意义,所以人生要去寻求它自己的意义,所以父母要给他(她)一个希望,把这个希望作为他(她)的名字。
如果在宗法社会,人生的意义取决于你在伦理关系中的位置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士大夫家庭出身的长子,那么你大概要实现“三不朽”。因此在宗法社会中,给人起名就是要论资排辈。
可是神话时代里面的人生意义是先天给定的。所以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去读取先天给你的那个命运到底是什么,然后把它强化下来。
屈原的父亲他也是楚国的贵族。屈原的父亲就解读了他出生的寅年寅月寅日这个特殊的时间,根据天命来给屈原取名。于是就产生了第四句奇怪的话,叫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王逸说这一句其实有一点像一个字谜。他说“正则”这个“则”就是“法则”的“则”,意思是效仿。所以屈原的父亲认为,屈原的天命是要效仿那个最正的东西,而那个最正的东西就是天,所以他的父亲认为屈原生下来是要来效法上天的,他有这样的命运。所以给他取名为平,因为就是“正平可法”的意思。
然后屈原的父亲又给了他一个字。其实屈原的字不叫“灵均”,而叫“原”,为什么屈原说“字余曰灵均”呢?因为“灵”就是生灵,“均”就是均匀。屈原的父亲认为他的儿子生下来是要像大地一样来均匀地养育万物的。什么东西才可以最均匀地养育万物呢?那就是大地,所以就取“高原”、“平原”的“原”字来作为屈原的字。
所以屈原的天命如此,而且他的父亲给他命名的方式强化了他的人生意义就是上能安君、下能养民。
正因为屈原的《离骚》的前四句讲了他的命名的来源,所以就使我对于一句话产生了质疑。我们讲到屈原常常会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如果屈原真的是那样的一个人,他会觉得他需要众人跟他的命运一样吗?需要众人跟他的觉悟一样吗?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关于“世人皆醉我独醒”:我们现在能够在最早的可靠的文献里面看到这句话,是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里面。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已经很难来理解这种基于神话时代的天命观,所给不同的人命定不同的人生责任的这样一种观念。
屈原只用一句来讲他的成长,就是第五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他说,我之所以要努力地学习来锻造自己,前提是因为我有“内美”。这个内美跟我们后来说的内在美它不是一个东西,这个“内美”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先天命定。
所以大家如果看过讲原始部落的动画片也好,电影也好,原始部落中只有那个智慧老人或者巫师是成天在学习的。我们永远不会在一个讲原始社会的电影中看到说那些奴隶、普通人在工作之余,他们还拿着一本书在看。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责任,在他们的时代里面,他们也没有学习知识的机会。
而屈原说我有这样的“内美”,所以我必须要增加我的“修能”。因此从比例上我们也会看到,他讲天命的部分很多,他讲后天成长的部分很少。
等到他讲完这五句之后,《离骚》就进入了很奇怪的一个阶段,就是讲完了出生,讲完了成长,马上就开始了枯萎。这就是第六句和第七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这两句其实是非常典型的《离骚》的片段。因为《离骚》的片段总而言之讲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披花戴草,第二件就是时间来不及。
为什么他一披上花草,就要讲时间来不及了呢?
“汩”字的意思就是水流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这是一个环形时间失落、线性时间开始的时代。屈原当他披挂上花草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时间是像水流一样往同一个方向流,而且它永远不会回来。因此在这种时候,花草就不再是《礼记·月令》里面那种秋天凋落、春天会再繁盛的花草,而是一种一旦凋落就永远凋落这样的花草。
所以《离骚》一开始就讲到了时间来不及,然后屈原就(写)“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在同一天里面,我早上去采摘的时候还是春日,我还可以摘到木兰,可是到这一天的傍晚就已经没有任何的植物了,只剩下寒冬的宿莽存在。它是讲时间的流转之迅速,讲的是在一天之中就好像经历了四季的感觉。
所以才会有下一句,叫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以及《离骚》中间很重要的这一句,叫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意识到,不但留给这些植物的时间很少,留给我们这些人的时间也非常非常地少。所以《离骚》的开端是这样的十句话。
众芳芜秽 他所有的草都是春风吹不生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众芳芜秽,一个真正彻底死亡的这个感觉。
屈原为什么会发现环形时间突然破产了呢?
《离骚》的前三分之一到底在写什么?一半是在写花花草草,还有一半全部都是在吐槽历史。吐槽历史吐槽什么呢?大致就是吐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应该得到奖赏的人没有得到奖赏;第二件事情,应该得到惩罚的人没有得到惩罚。
所以《离骚》的前三分之一里面有一半是你读起来很不愉悦的,因为你觉得它非常地唠叨、非常地计较,然后不停地在讲这个人没有好报、那个人没有好报。
事实上《离骚》正是在对历史的记载中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礼记·月令》时代的那种一切各安其时、各在其位就会受到上天的护佑,如果你超出了这个位置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更新能力,它结束了。
所以屈原他在《离骚》前三分之一写历史的部分他写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讲一种信念。他说我们以前对于历史的信念就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意思是说皇天它是非常公正的,它是冷静地审视在世的这些人,然后它选择那些有德性的人,给他们赋予特殊的命令,而且皇天会帮助他们。
但是这个信念破产了。因为他观察史实,屈原说我“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计”就是开端,“极”就是结束。所以他是说我瞻前顾后,来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开端和结束是什么样子的。而屈原自己观察的结果是:“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就是我觉得是那些正义的人才可以被任用,可是后面他写了一大堆正义的人没有被任用;然后我觉得那些善良的人才可以被人信服,可是他后面写了一大堆,常常是那些不善良的人他们谋取了高位。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信念跟史实观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错位。在这样的一种错位之下,其实屈原就发现了,神谕它不再灵验了,时间不再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善恶不彰的、天道不彰的一个堕落的世界。
03 《离骚》中的神仙世界与纯粹精神世界
《离骚》的第二个部分:寻回时间的秩序
第二个部分是从“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这句话开始的。
在这之后,屈原就迅速地飞翔,飞翔到了神话和上天的世界里面去。而且下面就开始了《离骚》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朝发轫于苍梧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它的意思是说屈原驾驶着玉龙和飞凤,然后这个玉龙和飞凤就带着屈原腾起,而且当他们腾起的时候非常有气势,天地之间就尘埃密布。
1970年《长沙子弹库楚帛画》
这幅帛画描绘的就是戴着长冠、身携长剑的这样一个人,他驾着玉龙要上征。就是我们看到的“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的这样一个景象。
现在的学者说这幅帛画被发掘的时候,它是在内棺的棺椁和外棺之间的一块木板上的。所以他们认为这幅帛画的作用,是在出殡的时候起到灵幡的作用,是为了引导灵魂上升。
屈原模仿这幅帛画,用一种在当时的丧葬仪式中讲走向死亡的这样一种形式,来讲自己的这一次追求。在我们以前的阅读中,我们以为他的追求是走向自由。但是我们现在结合这个文物来看,这个自由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是一去不归。
在这一次驾着龙凤上征之后,屈原去了很多的地方,这就是《离骚》中最动人的一长段。
他先去了最西的太阳洗澡的咸池,然后又到了最东的太阳升起的扶桑。他去了很远的崦嵫山,而且让月神(叫做“望舒”)来给他开路,然后让雷神(叫做“丰隆”)来为他当前导。
他要赶在时间结束之前达到天堂的门口。然后他到了天堂的门口之后返回到了东方春神的花园,因为东方的春神是掌管生命之神。他到了春神的花园。从春神的花园出来了之后,他又去了上古寻找了高丘的神女和落水的宓妃。然后他又去找了上古的有虞氏的女儿和有戎氏的女儿。所以他进行了一个这样丰富的行游。
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的陈世骧先生。他对于这一段的解说中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喜剧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帝阍。
帝阍就是神话里面给天堂看门的那个人。
在这一段里面,当屈原赶在时间结束之前到达天堂的门口,而且他几乎就要进入天堂,那个代表了所有美善、代表了所有理想的对象就在天堂之中的时候,屈原就说“吾令帝阍开关兮”,我让帝阍开门,我命令帝阍开门。可是帝阍“倚阊阖而望予”,阊阖是天堂之门。帝阍不给他开门,而且那个帝阍就靠在那个门上,他也不说什么,他就懒懒地看着屈原。
所以陈世骧说,这个天国的仆人他想要干什么?他可能只是懒惰,或者他只是无聊,或者他只是跟人间的看门人一样,想要一点贿赂而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时暖暧其将罢兮”,就是天堂的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屈原没有能够赶在那个时间结束之前进入到天堂之门。
在此同时,曾经驱使屈原陷于失望的人生如寄之感,现在又极其强烈地催促他上路追索。因为紧接着便是一句富于灵感的诗句:“时暖暧其将罢兮。”所以天堂的时间也失落了。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说他考证了屈原从天堂折返之后去寻找的那些女神,发现那些女神她们都属于是商朝始祖神话中的神。而且屈原去找这些女神的时间顺序是:他先去找那些离他的时代比较近的,然后再去找那些离他的时代比较远的。
所以小南一郎说,屈原在这里有一种他要逆回历史时间,回到时间源头的感觉。
屈原找到了所有这些女神。可是这些女神她们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有一个人理屈原。所以他们好像就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里面,屈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原初时间里面去。
这样一来,在《离骚》第二部分的最后,屈原就说“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他说,我带着这样的情感,我就是不能够忍受,我不能够忍受什么呢?“终古”在古代汉语里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结束,一个含义是永远不结束。所以这里可以同时取两个含义,就是我带着这样的遗憾结束,我也不愿意;我带着这样的遗憾永远不结束,我也不愿意。
所以在这个时候,屈原他想要进入天堂之门,没有进得去;他想要去寻求商朝始祖神话中的女神,回到时间的开始,没有回得去;而他发现,天堂的时间也跟地下的时间一样被污染了。
《离骚》的第二部分以屈原对神界的失落结束。
《离骚》的第二个部分里面比较有希望,比较有秩序,比较有光明。但《离骚》第三个部分的开始是相当诡异的,因为《离骚》的第三部分是以“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开始的。
从第三个部分开始,屈原就找来了两个巫师,女巫的名字叫做灵氛,男巫的名字叫做巫咸。他让这两个巫师为他占卜。可是两个巫师他们给屈原的建议,那是非常诡异的建议。两个巫师都给了同样的建议:第一,你没有做错;第二,你还不够极端;第三,你不要指望任何其他的神,你只能靠自己,所以你赶快上路。这两个巫师给了他这样的建议。
而且他们为了催促屈原上路,还给他占卜出了上路的时间,让他赶快走。屈原其实开始很质疑,因为他在第二部分受到了大量的挫折。可是他们现在说你还要去,他其实是很犹豫。
可是在他犹豫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时间的堕落变得更快了,就是后面的两句“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我们在第一部分看到的只是香花美草的凋落,可是到这一部分,“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荃蕙香草,茅是恶草,所以它不是香花美草凋落了,而是香花美草转化成了恶草。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屈原居然发现自己必须立刻上路,因为情况变得更严重了。因此屈原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远游。
第二次远游和第一次不同,这次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寻求的目标,就是完完全全一个人上路,而且他所去的地方都是神话中间的极西的无人之地。
他先去了积雪的昆仑山,然后去了银河,然后去了世界最西的流沙河神话中间“共工怒触不周山”的不周山。然后屈原说,在不周山旁边有一条积雪的唯一的天路,然后他去了西海。
在第二次的远游中间,第一,屈原是以一种更加极速的速度飞身;第二,他是完全没有伴侣;第三,他带着一种自我放逐的、有去无归的悲壮感在整个的世界中间行游。
他是以一种决绝的勇气在往各个方向飞奔。而且屈原有很多这种氛围的描写。他讲他所驾驶的龙凤,他所乘坐的极其华丽的车盖上面的銮铃发出的摇动不安的声音,以及跟随在他身边的云霓。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极其不安的气氛。可是在这个气氛里面,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神。
小南一郎说:“屈原在此时自己成为了唯一神,他获得了充满喜悦的永恒时间,不再受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困扰。”这个时候屈原他几乎就要接近永恒。
我很喜欢这一段最后结束的四句话,叫做“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为什么呢?因为屈原他马上就要接近那个时间的开端,那个未曾污染过的原初时间。
“陟升皇之赫戏兮”,因为“升皇”是初日之名,初升的太阳名字叫做升皇。“赫戏”是指它的光明。所以屈原说,当我马上就要接近初升的太阳的光明了,当我马上就要走近它了,而且我已经听到上古的《九歌》和《韶》乐。《九歌》是上古夏启的音乐,《韶》乐是上古舜的音乐。它们代表的都是神话中的那个理想时代。屈原说自己马上就要走近那个理想时代,可是在这个时候让我慢下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次缓行,《离骚》的节奏忽然间舒缓了下来。
“抑志”就是说让我按耐我内心的喜悦,“弭节”是说让我控制我的马,让它慢慢地前行。“神高驰之邈邈”是说我虽然现在有一个极其高的速度,虽然马上就要接近那个永恒,可是这个时候让我保持我的头脑清醒。
所以我们又会看到一个很可贵的东西,就是在《离骚》的第三部分开始,其实屈原在巫师的蛊惑下有了一种高度亢奋的精神。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开始变得清醒,那是因为他快要达到他的理想世界了。
《离骚》为什么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屈原写了一句非常不可思议的话,就是“忽临睨夫旧乡”。这个即将走到天堂门口的人,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看到了尘世的旧乡。而且他忽然间发现那个污浊不堪的尘世居然就是他的故乡,是他的所来之处。
当他看到了地下这个污浊的世界的时候,他又同时看到了另外的两个东西,就是后面那两句:“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我们看到这里会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在《离骚》的前面的所有部分,我们不知道屈原有一个仆人,我们也不知道他还要骑马,他不是都是乘龙的吗,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时候忽然间发现,他有一个跟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那样一个悲伤的仆人和一匹很疲倦的马。
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之前屈原完全没有看到他们?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在神话时代里面,像屈原这样一个深受天命的楚国贵族,他和他的仆人完全处在天壤相隔的两个阶层,我们就知道在《离骚》的前半部分,其实是没有一种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一种普遍的人性的,也不可能有一种普遍的人的关怀。
只有当屈原发现神话失落之后,屈原失去了神谕的加持之后,他才发现他的命运和芸芸众生原来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看到他的仆夫和他的病马,他才能够产生对于普通人的命运的怜悯。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才说了这样两句话。
正是因为屈原看到了那个污浊不堪的尘世的土地,并且承认了那是他的故乡,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命运,他做出了选择,就是我不进入永恒,我回到我的芸芸众生的命运中间去。
因此《离骚》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就进入到“乱曰”的那个阶段,“乱曰:已矣哉!”,屈原说,一切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之后要怎么样呢?“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再吐槽一下他的现实生活。但是,现实这么不完美,可是我愿意“从彭咸之所居”。彭咸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人,他是上古的贤人,投水而死。屈原说我也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贤人的命运。
现实意义:
关于屈原,一百多年来,因为各种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有人认为《离骚》是写一种同性恋情感,有人认为《离骚》是写一种自恋人格障碍,也有人认为《离骚》是写一种精神分裂的体验。这样的阐释和古代的“美人香草”的阐释一起构成了《离骚》阐释的多个声部。
可是我还是愿意把屈原看做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门槛上的人。他碰到的问题就是,不但是环形时间失落了,原先时间体系中的那种善恶观念也失落了,所以屈原需要在新的时代里面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准则。
其实他不是没有机会重新进入神话,他其实离进入神话世界只有一步之遥,或者用一种我们现代的说法,就是他有可能逃避到一种精神分裂性的幻想中去。甚至在他那个时代,这都不能称之为精神分裂。可是屈原抵制了永恒和极乐的诱惑,去领受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众芳芜秽,就是终将和草木一起凋落。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事情,但是屈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普通人的命运,他才把自己变成了理性时代的一个人,才能够成为后世士大夫的“偶像”,而不是成为一个传说中的巫师。
托尔·金在《魔戒》里面有一段话说:“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者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
屈原接受了礼物,而《离骚》正表达了人类在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的那种既充满了艰难、但是又充满了尊严的过程。
第二讲 曹丕:欢乐深处的忧伤
01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与王子的友情
公元前430年 雅典的瘟疫《俄狄浦斯王》
在公元前430年,在雅典发生了两场大瘟疫。诗人索福克勒斯受到启发,就以瘟疫为背景,写作了著名的《俄狄浦斯王》。
他设计了一个很具有悖论性的开端。因为俄狄浦斯王恰恰是以他的智慧回答了狮身人面的女妖斯芬克斯的问题,所以他成为了忒拜的僭主。在他统治之下,忒拜风调雨顺十五年。可是在十五年之后,忽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瘟疫。
这一次,俄狄浦斯王没有办法再通过他的智慧、他的理性来拯救城邦,所以他不得已只能够去寻求神的帮助。《俄狄浦斯王》这个故事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它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如何在命运面前反思理性的傲慢?
建安22年的瘟疫
建安22年,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瘟疫。建安是东汉的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是曹操以丞相的名义来主管天下的政权。
东汉末年是瘟疫的高发期。根据历史书的记载,从建安初年到建安22年,总共发生了五次大的瘟疫,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这么多的瘟疫的发生,它在文化史上首先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它导致张仲景写出了《伤寒论》。
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里面就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家族是很大的,向来都会有两百多个人。可是自建安年间以来,还没有达到十年,这两百多个人中间就有三分之二已经去世了,而去世的人里面又有十分之七是因为伤寒而死去的。
曹植 《说疫气》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意思是说,建安22年的一场瘟疫之中,中原的家族中间几乎就没有可以幸免的。几乎是每家人家都会有人好好地活着然后就仰面倒下了,每个房间里面都传出来哭泣的声音。因为瘟疫有传染性,常常是一个人遭受瘟疫,整个家族都受害,很多的家族就因此而灭门了。
可是曹植这篇《说疫气》后面写得很有意思。曹植说,据我观察,这些受到疫气伤害的,主要是那些衣食无着的贫困家庭,富裕的家庭往往不太受到疫气的伤害,为什么呢?他后面讲了一通很科学的话,他说疫气的流行是因为寒暑失调。那些愚蠢的百姓,他们以为瘟疫是温神、厉鬼带来的,所以他们把桃木刻成符,挂在门上,希望以此来躲避瘟疫。这当然是没有用的。
曹植的《说疫气》在后来有很高的评价,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很唯物主义,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很关心民间疾苦。
在建安22年的这场很大的瘟疫中间,有四位很重要的诗人去世——“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我们现在去看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那些交往的文章,会发现曹丕也好,曹植也好,他们和“建安七子”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都是朋友关系,可是曹植没有提到这样一件事情。
建安22年的这场瘟疫,它不但带走了“建安七子”中一半以上的诗人,还改变了文坛的整体风格。如果我们要背文学史,文学史就说建安文学的前期和后期不一样:建安文学的前期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可是后期就变得消极,就表达了各种生命短暂、生命无常之感。这样的一种变化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瘟疫。
“建安七子”文学的自觉时代
根据鲁迅的一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的说法,他说“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就是他们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什么叫做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是说在建安年间之前,没有人认为一个人可以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追求。我们会看到《诗经》,也会看到《楚辞》,可是我们不知道《诗经》的作者是谁,因为它没有署名。《楚辞》我们知道它有一部分的作者是屈原,可是屈原他没有想要把诗人作为他的人生目标。
到了汉代,有汉乐府,汉乐府写得很好,很多是文人写的,可是它没有署名,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一直到了东汉末年有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写得是精美绝伦,而且它的质量是相当地平衡。后来的这些文学评论家,他们把他们能够想到的所有最好的话都拿来表扬《古诗十九首》。比如说像《文心雕龙》就说《古诗十九首》是“五言之冠冕”,所有五言是中间最好的。《诗品》就说《古诗十九首》是“一字千金”。明代的胡应麟说,这些诗它只是诗而已,可是它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到清代的陈祚明就说《古诗十九首》是“千古至文”。
可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古诗十九首》,我们还是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好像它们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完全没有这个需求要给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
“建安七子”开始给他们自己的诗歌署名。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追求之间的那种对应关系。从此之后,文学史就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人的个性表达,它开始追求个人的风格差异,它要留下个人的生命的痕迹。
这就是“三曹”和“建安七子”他们给文学史提供的一种重要的影响。
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发展到建安时代,一千多年,人们终于走进了那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可是在一场瘟疫中,“建安七子”中间的四个就去世了。
曹丕 《与朝歌令吴质书》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碁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呜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今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行矣自爱。丕白。
大概在魏晋以前,是没有像晚明的袁宏道、张岱那样有意识地来写作抒情散文的这样的作家的。所以魏晋时代的抒情散文其实就是私人书信。我们现在如果要去找魏晋时代最接近于抒情散文的东西,就是在《昭明文选》里面的《书》这一部,“书”就是指书信。
正因为这样的一些文本,在写作它的时候,不像后来的人那样有一种要去写给大众看的意识,就是一种很私人的表达,所以它反而表达出了一些最私人、最真切、最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感。
曹丕他这个人,他不管是写诗还是写文,都有一种特别沉静、优雅、温厚这样一种调子。
所以我们看第一段,他其实是在一个夏初的时候写的信,曹丕当时是一个王子的身份,还不是一个太子。他写给当时在当朝歌令的吴质。吴质的字叫做季重。朝歌在什么地方?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南淇县。所以是一个王子给一个淇县的县令写信。
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吗?我和你之间隔得没有很远。其实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还是有点近。可是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官职之上,也不方便经常走动,因此“愿言之怀,良不可任”。
他说因此我对你的这种思念的情感常常是难以忍受的。而且“足下所治僻左”,你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还是很偏僻的,因为偏僻,所以我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变得越来越少。就“益用增劳”,“益用增老”就是说让我对你的思念变得更加地强烈。
这封信的主体部分其实是第二段,就是“每念昔日南皮之游”,南皮在山东的北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起在那个地方玩耍。所以这封信的第二段它写的主题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玩的。
他说是“妙思六经,逍遥百氏”,这两句是讲读书,六经是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妙思”是说深思。他们虽然读儒家的书,对儒家的书很尊重,但是儒家的思想它不是统治性的,不是排他性的,所以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在诸子百家中间选择去阅读。所以他们讲读儒家的时候比较尊重、比较认真就是“妙思”。而当他们去读诸子百家的时候就比较自由,那就是“逍遥”。所以就是“妙四六经,逍遥百氏”。
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读书,在读书中间他们还做游戏。游戏就是“弹棋”和“六博”,“弹棋”和“六博”都是带有一定赌博性质的棋类游戏。可是他们又不沉溺于赌博之中,因为他们一边在玩,一边还在聊天,还一边在高谈,进行义理性的探讨。而且他们的耳朵还听着音乐,听着哀筝的音乐。
一般来说,我们高谈阔论都是为了展示自己,为了争夺胜负,为了炫耀机辩。可是高谈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娱心”的程度,它就有一种心意相通、心心相惜之感。
而他后面讲到“哀筝顺耳”,这也写得很好。因为他不是说我们去听快乐的音乐,不是去听悦耳的音乐,而是去听哀伤的音乐,而这个哀伤的音乐不是来取悦你的,它是让你觉得顺耳。
这里面就好像是,在一种快乐的极致的时候,反而需要一些哀伤的音乐,他才能够去共情那个心灵的整体。这是曹丕以他特有的敏锐性和他的语言的准确性所写出来的话。
前面是讲在读书的时候,讲的是一个比较静态的活动。后面就讲更加带有青春动感的一段生活,就是“弛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这个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讲贵族青年的游宴和游猎的生活。
曹植《名都篇》 感官的刺激 充满活力的快乐
曹丕和曹植的诗文写得非常地不一样,可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常常是一样的。所以曹植在他的名作《名都篇》里面这样写(因为《名都篇》很长,我们就看其中的一部分):它的上半部分就是写“弛骛北场”,下半部分就是写“旅食南馆”,可是曹植他是怎么写的呢?他是从外在写的,他是铺陈景物的,他是追求气势的。所以当你去看曹植写的这些文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你会觉得他的那种推进非常地迅速,它会带给你一种活力。
所以当曹植来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这段话,他说是“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没有人像他这样写,他写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这些贵族青年早上出去玩,早上我们还在东郊这个地方斗鸡,可是斗鸡它又不讲结果,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好了,所以他们不是那么争胜负的。可是斗鸡斗了一半之后,忽然觉得跑马也不错,就跑到树丛中间去跑马。然后跑马也才只跑了一半,忽然间看到两只兔子从前面跑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跑去追兔子。他们追兔子的时候,他们是用那种很夸张的、就是上面带着哨子的那种箭,所以他们拿箭去射的时候就会有很好听的声音,非常地有气势。他们一边射兔子一边就这样上了南山。可是我们要知道开头的时候他们还在东郊,这个时候已经跑到南山去了。
他有没有追到兔子呢?这个事情也不管了,因为他忽然间又看到了天上飞过去的鸟。 而曹植又是非常喜欢在诗里面炫耀自己的武艺的。他说他的武艺特别好,他就“左挽因右发”,就是他骑在马背上,然后先往左去瞄准一下,然后往右去瞄准一下,最后发现往右瞄准那个角度比较好,他就射了一支箭出去,一箭双雕。然后两只鸟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曹植的写法。你读他的诗你就会觉得很快乐,你也不知道快乐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那种不断推进的速度,他那种在每一句中间给你不同的感官的刺激,就会带给你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
而曹丕他不这样写,曹丕就写四个字,就是“弛骛北场”就好了。所以曹丕他是从内在来写的,他不太给这种感官的诱惑。
下面曹植就讲说,我们白天不是已经游赏完了吗?游猎完了吗?那晚上我们就要去吃饭了,吃饭是什么样的呢?“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这十个很难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鲤鱼切的鱼生,就是鲤鱼的生鱼片,还有虾羹,还有爆炒甲鱼,然后还有烤熊掌。
曹丕 作为生命底色的哀伤
同样是食物,曹丕怎么写?曹丕就写“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他只说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甜瓜,一个就是李子。可是这两句话里面,他把那种甘甜的滋味,那种朱红的颜色,那种泉水的清凉,那种夏天的环境全部都写到里面去了。
在完成了这样的旅食和游宴之后,曹丕他要写我们是如何经过一个白天进入到夜晚中间去的。李白写《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里面就说“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我们白天玩够了,晚上还要继续来玩。所以曹丕下面就写“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从白天进入到夜晚的这样一个过渡。
前面不是都在写快乐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决定到夜晚中间去继续白天的快乐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沉入到了一种忧伤的情感中间去。
所以这个时候,那些马车的车轮就开始变得很慢很慢。那些跟从他们的人,跟从他们的人在那个时代被设定为是不像这些贵族子弟这样敏感的,是比较愚钝的,可是这些跟从他们的随从,他们居然也好像受到了感染,他们也不发出声音。这个时候他们就感到了夏夜的风的吹起,他们就听到了很远的地方的胡笳的乐声,而且是悲哀的乐声。
所以曹丕就再一次说“乐往哀来,怆然伤怀”,其实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没有任何契机的,他就觉得哀伤又到来了。
这个时候曹丕他就“余顾而言”,他就看着他的那些朋友,跟他们说“斯乐难常”。“斯乐难常”是曹丕当时说的话,说我们的快乐是不会长久的。可是曹丕这个时候才只有二十几岁,一个二十几岁的王子他说这样的话。
在很多年后曹丕要给吴质写这封信,说“今果分别,各在一方”,你看,我当时那种“斯乐难常”的预感成真了吧?我们今天果然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而且我们当时一起玩耍的人中的“元瑜”,就是阮瑀,他已经在建安17年的一场瘟疫中间死去了,所以他说“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曹丕写这封信给吴质,他其实是要表达一种生命的虚无之感。相比于短暂的人生的快乐,死亡显得无比漫长;相比于荣华富贵来说,人死后你甚至不能说他变成了什么,所以曹丕只能说他化为异物,化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连化成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
曹丕写了这封信给吴质之后,吴质给了他什么样的回答呢?我就去查了吴质的文集,然后就看到吴质给他回了一封信。前面的一半是说,年轻的时候和太子你一起游玩真是太荣耀了,然后后面说你不要忘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就把我调回到首都去,不要让我在这里当官了。然后对于曹丕在书信里面写的所有的多愁善感吴质一句都没有提。
然后又过了三年,曹丕又给吴质写了一封信。他这封信写在什么时候?就是写在建安22年,就是建安22年的那一场瘟疫结束之后,他给吴质写信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曹植讲建安22年这场瘟疫的时候,他说富贵之家不受伤害,只有那些愚蠢的穷人才受伤害。可是曹丕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认为他有很多的“亲故”在这场瘟疫中遭受了灾害,而且他感受到了这场瘟疫对于他个人生命的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就是“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徐、陈、应、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建安七子”中间的四个。所以他说“痛可言邪?”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是写的叫做“痛何可言邪?”写得要更加深切,就是,我这种痛苦就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后面他又把前面那封《与吴质书》里面的话重新说了一遍,说得比较简单一点,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他后面又说,我们当时是“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当时那么年轻,那么欢乐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被赋予了一百年的寿命,然后在这一百年之内我们是可以互相珍爱,互相保重的,这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可是没有想到,“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哪有一百年?只有几年的时间,人已经剩得差不多了,所以是“言之伤心”。
曹丕就说这些人死了,我做了什么呢?我就把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编成了一个文集。可是当我把这些文集打开,我在看姓名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成为“鬼录”了。陶渊明的诗里面说“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所以我觉得陶渊明其实在写作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曹丕的影响。昨天我们还是朋友,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录鬼簿。
“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他现在说他们已经化成了粪壤。
这封信后面的大部分都是他一一地回忆这些朋友他们个人的人格特征和他们的文学特点。写完之后他就说,说他自己,他说我虽然才只有30岁,我的头发也没有白,可是我的心已经像一个老翁一样了。而且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有像昔日那样地游玩了。他就把这封信写给了吴质。
那么吴质是怎么样回复他的呢?吴质继续写了一封信,前面又说了一通,当时跟太子一起游玩真是太荣耀了。然后后面就照着曹丕表扬那些人的话,把那些人表扬了一遍。最后提醒曹丕说,你有机会的话不要忘了,给我升个职,就是这样子。
以文学对抗生命的虚无
曹丕对吴质失望不失望不知道,反正我是对吴质挺失望的。但是我觉得曹丕是不满意这样一种回复的,所以曹丕又和王朗写了一封信。曹丕在给王朗的信里面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所以我们会发现,曹丕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一个非常敏锐的感受,一个非常通透的认识。就是他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他是一个太子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能够意识到,我是什么特别的人吗?如果所有人所遭受的命运都是那样短暂脆弱的,那么王公大臣也没有办法幸免,为什么我偏偏就是能够长命百岁的人呢?
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就会讲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文献,就是《典论·论文》。曹丕在建安22年这场瘟疫发生之后当年,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特殊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我只有靠文学写作,才能获得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他当年就写完了他的这部著作,就是《典论》。
《典论》我们现在不能够全文看到了,有些遗失了,但是我们可以看里面的《论文》一篇。《论文》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其实是很惊世骇俗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是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把文学的地位放到一切东西之上,甚至把文学的地位放到建功立业之上,放到治理国家之上。他说人生是有限的,可是文章是可以无穷的。所以《典论·论文》中的这句话,是中国从古至今所有文献里面对于文学价值给出的最高评价。
曹丕希望靠文学解决他的人生困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看曹丕的作品、他的诗文,我们其实在其中没有能够看到文学真的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他的诗文中其实很少有那种解脱的欢喜,更多的还是生命的哀叹。
02《燕歌行》: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见呼喊
曹氏父子他们三个人的诗歌各不相同。曹操他更多是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勇敢的呈现,而且他有一种改变的志意在里面。
顾随先生他就说曹操是有力的诗人,他的诗中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力量感。但是曹丕的诗中间也有很多生命的哀叹,曹丕不大从现实的层面来写,他很容易就进入到存在的层面。他很容易会把这种生命的脆弱性、短暂性和人生的虚无当做一种生命的本质来写,所以曹丕的作品不太像曹操那样比较多地停留在现实的层面上。
曹丕有一首诗叫做《大墙上蒿行》。曹丕作为诗人比较可怜,因为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不认为曹丕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忧伤的。所以顾随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历史上人皆痛恨文帝而同情曹植,其实他那位弟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所以顾随看起来是他是有多么不喜欢曹植才说这个话。当然如果你去看顾随的书,你会发现他还是很公允地说了曹植的诗文在文学上的好处,但是在性情上他显然更接近曹丕。
生命凋零的绝对性
《大墙上蒿行》是乐府旧题,大概它的本辞讲的是墙头上的那个蒿草。草长在墙头上,它是比较无根的,是很容易会衰落的这样的草。
曹丕的《大墙上蒿行》说:“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这是开头。
我们看这一首诗,其实会和我们读一般的古诗的感觉不太一样。一是它里面的句式,它是六言、七言、八言这样的一个杂言的组合。第二,它常常是三句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式,所以读起来的感觉其实是比较拗折的感觉。
“阳春无不长成。”它讲的是说,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在那个春天的骄阳之下,一切的东西都在成长,不管你是墙头上的蒿草,还是苍松翠柏,你都长得很好。当他用这句话来讲一种生命感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他对生命的感觉不是他通过学习、通过教养得来的,他就像一个外星人,被孤零零的扔到地球上,然后他第一次发现原来生命是这样的,非常原始的,在阳春下面,它们就是会成长的。
可是,立刻就发生了一个转折,就是第二句:“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你前面不还是阳春吗?不还是没有条件的、不需要努力的、不需要浇灌的你就长成了吗?可是马上大风一来,一切东西都被吹散了。在这样一种转折之中,就带来了一种时光流逝、生命凋零的绝对性的感觉。
如果说你是一个感受到了这种生命凋零的绝对性的人,虽然你还没有自己亲身遭遇到,那你去如何看待你下面的生活?你是把它看作是阳春,还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凋零的前奏?
所以他写了下面的两句,第一句说“中心独立一何茕”,我站在天地的中心,可是我觉得我是那么孤独,虽然我是一个王子。而且我觉得“四时舍我驱驰”,春夏秋冬它们都飞速地离开了我。“今我隐约欲何为”,“隐约”在这里是痛苦的意思,那么我的痛苦怎么办?曹丕是一个帝王,可是他表达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孤独感。
下面有一个比喻,他说“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他说我们的生命在巨大的天地之间,好像是一只鸟停留在枯枝之上。枯枝是非常容易折断的树枝,因此“我今隐约欲何为”。他稍微改换了一下表述。
所以我们把第三句和第四句对起来看,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第三句讲的是一个帝王,然后第四句讲的是一只站立在枯枝上的孤鸟,可是他们之间是一样的,他们之间有一种对偶关系。
这就是曹丕对于生命的感觉。
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自我说服。其中包括说,那么我们就去穿那些最好的衣服吧,那么我们就去吃那些最好的东西吧,那么我们就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旅游吧。甚至还有后面的,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变得非常地有修养,我们就把自己变得非常地优雅、非常地有仪态,在人家的眼里面变成一个很好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行不行?
他最后说“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所有的自我说服都没有用,一切都破产了,他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大墙上的蒿草。
清代的张潮在《幽梦影》里面提到过一个人生的大满贯理想,叫做:“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一般的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觉得我们只要获得了这一切,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曹丕获得的东西远远地超过这一切,但是他的所有的诗都是讲他的不满意,讲他的忧伤。因此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就要说,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矫情自视的人,不然他还有什么可以忧伤的呢?
所以曹丕,因为他的心灵的敏感性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要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叫做“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这是写得非常好的话,是非常具有语言天赋的人能够写出来的话。
曹丕讲的“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就是说,谁会第一个最敏感地感受到风的到来?是那个高山上面最高的那棵树最顶端的那个树枝,是那个最顶端而且是最纤柔的那个树枝,它第一个感受到风。如果你不是那个高山上的树,你是平原上的树,或者峡谷中的树,你会觉得没有风。或者说你是高山上的树,可是你没有那么高,你也会觉得没有风。可是,只有是最高的山上的那个树枝,当它感受到风到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理解它,没有人能够知道它,而唯独它知道这一场风,最后会刮到每一棵树上,会刮到每一根树枝上。所以他讲的是一种心灵极富敏感性的人,他对于世界的感知和其他人不同。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莫之知”很好理解,就是说别人不知道。“忧来无方”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说你不知道忧愁它会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来,你不知道忧愁它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临到你身上,可是如果要讲得深一点,就是说,忧愁就是生命的本质,就像空气的流动本来就会带来风一样,所以人存在、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就带有忧愁。
顾随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曹操是有力的作者,陶渊明是有办法的作者,他没有讲到曹丕。
我觉得曹丕能够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可是他没有办法来摆脱这种悲剧。他的敏感性能够让他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可是不能让他成为哲学家或者圣贤,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他感到的这种强烈的生之悲哀。
以这样一种强烈的生之悲哀为背景,曹丕写出了一种普遍的忧思,其实在文学史上曹丕最重要的四首诗是两首《杂诗》和两首《燕歌行》。
《燕歌行其二》
曹丕的诗歌差不多都有一种柔婉和美的特点。可是这首诗写得比较深情激越,写得比较强烈。而且一般的文学史说两首《燕歌行》都是讲思妇之情,一般思妇之情就是说我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他把我忘记了,所以思妇之情一般是一种怨情。
但是我们看曹丕《燕歌行》的第二首里面,你不大看得到“怨”,在第一首里面非常多,在第二首里面没有“怨”这个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悲痛和忧虑。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首诗里面好像可以看到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鸧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
“别日何易会日难”?它其实讲的是一种后见之明,就是当分别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觉得分别是很常见的事情,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你一旦“轻离别”了之后,在离别之中你再要见面,你发现见面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他才会有一种后见之明说,离别是多么地容易,可是见面是多么地困难。
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下,他就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阻隔变得非常地悠远,而且非常地险阻。离别变成了常态,见面反而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样一种无法见面的情况之下,他这里说“郁陶思君”,《燕歌行》第一首也是思君,可是《燕歌行》第二首的思君,里面是说一种思念夹杂着担忧,而且这个担忧因为没有地方去验证,没有地方去问询,没有地方去获得反馈,所以最后不得已只能去问天上的浮云。可是浮云都把问询的声音吸收掉了。这种没有反馈的问询、无法证实的担忧,就只能变成无声的泪水。而这样无声的泪水它所毁坏的还不仅仅是容颜,同时也毁坏我们的生命。
这里的“未敢言”、“往不还”和“独不叹”里面,都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所以当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里面说:“如果我呼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在这个时候,因为有担忧,因为有对于轻易离别的后悔,因为有这种无法证实的、没有反馈的这种压抑,所以曹丕他想换一个方法来自我调节,他就“展诗清歌聊自宽”,我来写一点诗,我来唱一点歌,我用这种方法来自我宽解。可是,当他这样自我宽解的时候,他又进入了那种他常常写的“乐往哀来”的感觉。
而这时候的“乐往哀来”他把它写得非常地强烈,他说是“摧肺肝”。这个话的感觉是很强烈的,就好像是我们用民间的话说“我的心也在痛,我的肺也在痛,我的肝也在痛”。
这是因为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内心的担忧没有结论,所以仅仅靠转移注意力来获得的快乐,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快乐的尽头就又是“乐往哀来”。他就又进入到那种“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或者说是“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的那种感觉中间去。
如果是像曹植或者是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当他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情感的时候,他一定会继续往前写,然后一波一波地把这种情感的强烈性表达出来。中国文学中间就说,那是一种往而不返的情感,一直往前走。
可是曹丕他不是一个这样的诗人,他是一个比较有节制、比较内敛的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他就跳出来,从客观的角度来写,就写“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他不去写这个人的内在感受了,他写这个人的外在观感,说他夜久无眠。然后就像李白的诗里面写的“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一样,他从夜间一直等到了第二天的天亮,等到了飞鸟的叫声。可是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又进入到第二天,就是下一个循环中间去。
如果我们要来讲这首诗里面一种更加微妙的感受,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声音关系。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他讲那种内心的压抑和痛苦,他有一个表达的机会,他有一个向浮云发问的机会,而浮云把他的声音吞掉了、没有给他任何的回馈之后,他就没有声音了。但是没有声音,其实我们看“仰看星月观云间”和“寄声浮云往不还”是两个同样的动作,但是他这时候只有看而无声了。
那么那个声音是由谁发出来的呢?第二天早上有一只孤独的飞鸟发出了那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人甚至还不如这只飞鸟,因为飞鸟还可以把自己的悲伤说出来,但是人不可以。所以在他的发声和不能发声的悲痛和压抑之间的巨大的张力,就是这首诗中非常独特的东西。也是只有曹丕能够写,曹植从来不写这样的诗。
正是因为不具体,所以这首诗中间表现的忧思就更加具有普遍性。它表达的大概是所有那些经历过惊惶的、不安的日子的人们那种共同的感受,那种音信不通、朝不保夕、内心痛苦、无处表达、无处纾解的体验。
以前的文学史常常说曹丕多愁善感,没有曹植和曹操诗歌的主题宽阔。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曹丕他更多地不是像曹操那样写“英雄之诗”,他也不像曹植那样写“才子之诗”,他更多地是写一个普通人的一种生命感受,所以他的诗歌比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都更有人情味。
在建安22年的年末,“建安七子”中的最后一个,就是王粲,他也去世了。曹丕带领其他的大臣去吊唁。在吊唁的时候,曹丕说,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我们就为他再学一次驴叫送行吧。然后曹丕就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间,首先学起了驴叫,向王粲送行。
三年之后,曹操去世,曹丕继任丞相和魏王。不久后,汉献帝把他的皇位禅让给了曹丕。曹丕想以汉文帝为标准,做一个宽仁玄默、无为而治的君主。他也基本上做到了。他只做了七年皇帝然后就死了。
在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推行颁布了息兵诏、薄税诏、轻刑诏,一个是平息战争,一个是少收税,一个是减少刑法。甚至在他为自己写的《营寿陵诏》——来安排自己以后的陵墓如何处理的这个诏书里面,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没有一个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没有一个皇帝的坟墓是不会被人挖掘出来的,所以“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皇帝,但是我所需要的那个棺材只是可以把我的骨殖放在里面,让它慢慢朽烂就可以;那那些衣服呢,只是让它保护我的肉体,不要在肉体朽烂之前衣服就朽烂了,就可以。所以他对于丧葬仪式的要求是非常低的。
所以在曹丕去世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棺材只漆三道、不要金铜珠玉陪葬、不要苇炭防腐。而且所有的寝殿,就是坟墓的地上建筑,它的墓道、园林,甚至封土,封土就是坟墓上面的土丘,所有这些都不需要,一切都不需要。而且他死后淑媛和昭仪以下的妃子全都放她们回家,任其另嫁。
这是发生在一个王子身上的故事。
帝王常常认为他们不是凡人,但是曹丕知道他是凡人。是瘟疫,使俄狄浦斯王去放下人间君主的傲慢;也是瘟疫使曹丕去认识“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对于这些占有人世最多的财富、最大的权力,甚至是最多的才智的人们,他们相信靠自己的理性足以掌管世界。可是瘟疫挫败了他们,使他们有机会认识人的局限,有机会去节制权力和自大,生民便因此受惠。所以这才是疾病给人们的礼物。
第三讲 陶渊明:生死的辨证
01 到柏树和陵墓那里去春游
《小约翰》 直面死亡
在这个童话里面,小约翰在一个仙女的带领之下,去沙丘下面的一个兔子洞里面参加一个晚会。可是他第二天再去那个沙丘的时候,发现那个沙丘下面只有一排腐烂的棺材。这时候就有人跟他说,你看,爬出来虫子来的那个骷髅,它就是昨天晚上晚会上最漂亮的女子。
鲁迅在翻译这个小说的时候,当时的现代汉语还不是那么完善,所以他的翻译带有一定的文言色彩。他把里面的死神翻译成“永终”,所以就有一个人向小约翰介绍“永终”。
永终说,你在寻觅我吗?
人们说,不,我们没有想要去寻觅你。
可是永终说,除了我,你们却不能够找到别的什么东西。
在那个故事的结尾,天使和永终在一边呼叫小约翰,可是小约翰听到另外一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与我同走人生艰难之路。所以小约翰就往人生的那个方向走。
作为一个童话故事,它相当地残忍。可是它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它去除掉了很多的文明覆盖在死亡上的油彩,去直接地观看死亡。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陶渊明用一种比《小约翰》更加天真、更加平易的态度来写死亡。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陶渊明就像一个小孩子写作文一样,第一句“今天是个好天气”,我们就要出去春游,所以就有下面的一句,叫做“清吹与鸣弹”。清吹是指管乐器,鸣弹是指弦乐器,所以这样一群人就在一个春天的好天气里面一起出去郊游了。这就构成了这首诗题目的前一半(诸人共游)。
可是这首诗题目的后一半有一点怪异,他们郊游的目的是“周家墓柏下”。因此下面会说“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柏下”是什么意思呢?古时候的坟墓上面遍植松柏,所以“柏下人”就是“墓中人”的意思。
陶渊明也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用一种非常天真的口吻问道,“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死去的人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呢?
可是陶渊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他没有继续纠结在死亡的问题上,反倒是回过去讲他们这次愉快的春游。
“新春”、“新酒”、“新声”,这都是极言其新。我们也会看到那个没有滤过的酒,它是一种粗酒。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没有伴奏的那个歌,它是一种徒歌,是极言其简单。所以这个“新”本身就构成了对于周家墓柏下的死亡象征的一种对抗。可是另外一方面,它有一种好像我们随便在生活中间就可以找到一些东西,让我们快乐起来的意思。
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两段长久的黑暗中间那个短暂的光亮,那么每一个春天和每一次郊游就变成了一个奇迹。
陶渊明的时代背景: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很糟糕,我们在大学里面讲中国古代文学课,有一个学期叫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文学”。讲这一个学期的时候,老师们都很抱歉,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期的前半段,所有的诗歌没有一首诗歌是快乐的诗。
我们讲这段文学会先讲到三国,讲三国的时候就先要跟学生说,三国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是曹操的诗。
三国时代结束之后,西晋开始,我们要讲“竹林七贤”。我们又要先跟学生说,西晋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是《晋书·阮籍传》里面的话。
在公元220年到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中间的这200年,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最黑暗的一个时代。特别是从东汉到曹魏到西晋,它不但是代和代之间的轮替。包括在西晋的每朝之间的轮替,往往是通过篡逆和谋杀的方式实现的。
西晋发生了那么多的内斗。在它终于灭亡的时候,它的北方被中原的匈奴占领。匈奴不但占领了长江以北,不但攻破了洛阳,在洛阳进行了屠杀;还把西晋最后一个皇帝带回到了匈奴的军中,然后让这个小皇帝穿着仆人的衣服在军中行酒,就是让这个小皇帝给大家倒酒,让这个小皇帝给大家洗酒杯,那是为了羞辱他。而且最后就把这个小皇帝杀掉了,他去世的时候才只有18岁。这就是著名的叫做“青衣行酒”。
这件事情给了西晋的诗人一个很大的刺激。最后在长江以北待不下去了,所以中原氏族就渡过长江,定都在金陵,这就建立了下一个时期,就是东晋这个时期。这就是著名的“衣冠南渡”。
我们在文学史上、艺术史上都很喜欢讲“衣冠南渡”。因为“衣冠南渡”这件事情之后带来了大量的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所以我们会在《世说新语》中间看到大量美妙的故事,会看到很多他们对于艺术的妙悟。
可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当时的民间,民间的感受不是这个样子的。因此我们看汉代和晋代的民间文学,中间更多的都是死亡,都是瘟疫,都是战争,全都是这样的事情。
陶渊明这个人他一生经历了三次换代。从陶渊明成年之后到他死之前的几十年时间,他首先是经历了公元403年的桓玄废晋安帝。然后公元410年,桓玄当了皇帝,国号叫楚,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桓楚,这个桓楚又灭亡了。桓楚灭亡之后,晋安帝就又被找回来当傀儡皇帝。
到公元419年,刘裕把晋安帝杀掉了。在杀掉晋安帝之后,他立了另一个傀儡皇帝,就是晋恭帝。可是才过了一年,刘裕觉得自己已经具有当皇帝的资格了,我不需要这个傀儡皇帝了。他就把这个晋恭帝杀掉了,怎么样杀的呢?让一个宫女去用一床棉被把他闷死了。
天道的失落
而陶渊明很奇异地被夹杂在这样一个变异的时代中间。他做过桓玄的幕僚,也做过刘裕的参军。所以我们常常说陶渊明为什么隐居,我想也和他很凑巧地与这些人有过一种主臣关系有关。
刘裕后来建立的时代就是南朝宋。我们如果去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对刘裕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刘裕的最大功绩是他把中国的版图又从长江以南推回到了黄河以南(就是推回到了黄河流域)。
所以梁启超也说:“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贱种世世为中国患,而我与彼遇,劣败者九而优胜者不及一。稍足为历史之光者,一曰赵武灵,二曰秦始,三曰汉武,四曰宋武”。这个“宋武”就是指的刘裕。
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大历史,我们会觉得刘裕有这样的功绩,可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时代生灵的生活,恐怕就要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在刘裕建立宋朝的同一年,陶渊明写了这样一句诗,叫做“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他觉得天道可能是处于越来越多的失落之中。
在东晋灭亡的次年,陶渊明写了另外的一首诗,叫做《述酒》。《述酒》这一首诗你表面上去看,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在写历史,但是事实上他是非常隐晦地在写东晋的历史:从晋室东渡,带着重建文明的理想到南方去建立新的国家开始写;写到中原陷入到匈奴之手;一直写到东晋的灭亡。这是在晋亡之后的第二年。
在晋亡之后的第三年,陶渊明写了著名的《桃花源记》。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只讲《桃花源记》,可是我们很少去讲《桃花源记》说里面的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事实上这个时候桃花源之外也已经没有晋了,晋已经失落了三年了。
02 擦掉涂在死亡上的油彩
那么在这个天道悠远、鬼神茫然的时代之中,怎样看待生死?
陶渊明在有一首诗里面写他年轻的时候,叫做“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那个时候还是东晋,而且离后面的不管是桓楚还是刘裕篡晋,都还离得很远。所以陶渊明也和所有的古代诗人一样,杜甫也写过这样的话,李白也写过这样的话,说我小时候我带着很多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我为了去做准备,为了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我走遍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最熟悉的陶渊明他不是这样的。我们熟悉的陶渊明是要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陶渊明。
陶渊明我们常常比较多地讲他的五言诗,但事实上陶渊明有一系列非常好的四言诗,而且他的四言诗比五言诗更多地、更完整地表现他自我的一种整体精神。
《归鸟》
在他的四言诗里面有一首叫做《归鸟》,就是陶渊明的一生的象征。《归鸟》有四章,是复沓的这样一种结构。
在《归鸟》的第一章里面说,我要远去的话我就要去八表。如果我只是停留在近的地方休息,我就找一个云中间的山峰停留。
看到《归鸟》的第四章,他说自己的时候,叫做“游不旷林,宿则森标”,就是说我要去远地方,我也不超过树林的边界;我要停留在一个近的地方,我就停留在树林中间的一棵树的树枝上就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种他的个人精神的变化。
面对自然,接近真实
其实在陶渊明的作品中间,他来表达他在中年之后的生活,主要更多的是在写耕种,在写人情,在写自然。因此我们常常会误把陶渊明当做一个田园诗人。
《归园田居》
所有的人都学过陶渊明的一首诗——《归园田居》的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然后最后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可是我问过我的学生,他们读完了高中之后,大家都很讨厌这首诗,为什么都很讨厌这首诗呢?一半的人觉得说陶渊明这个人太没有社会责任感了,还有另外的一半人说老师,我爷爷种过地,种地一点都不像陶渊明写得那样高兴,所以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诗。
但是事实上《归园田居》总共有五首,我们要把归园田居的第一首放到五首的整体框架里面,才能够理解第一首的意思。虽然它放在第一首,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最后一首得到理解的诗歌。
《归园田居》后面的四首在写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我选择的这几句。在《归园田居》第二首里面表达了一个感慨,叫作“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第三首就是著名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第四首里面有一句叫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对生命本身的思考
我们看到从第二首到第四首,就觉得好像不仅仅是在写躬耕田园,它好像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从第四首开始讲。
第四首说:“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这一首开始的两句叫做“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去”就是离开,“浪莽”书上的解释叫做放旷。什么意思?一般就是理解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参加山泽之游了,也很久没有去参加林野之娱了。这两句的理解没有异议,大家都是这么理解。可是异议在于它和后面两句之间的关系。一般的解释都是说,因为我以前去做官,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山泽游、林野娱,我现在归隐了,我可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可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关系是不对的。为什么我认为这个逻辑关系是不对的呢?因为如果我们往下看,看到陶渊明在自然中间的行游,他是在荒墟中间行游,而且他是要去劈开那些荆棘,自己去披荆斩棘,才能够在荒野中间行进一步。这真的是文人所说的山泽游、林野娱吗?这真的是同一种东西吗?
如果我们再说回到“晋室南渡”这件事情的意义。晋室南渡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中一个意义就是宗白华所说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深情。
所以一个合格的东晋时代的诗人,他应该像谢灵运一样,享受在名山大川之间游玩的乐趣。所以我们看谢灵运的诗,会看到大量的山水诗,但是谢灵运不会告诉你,他是带着几百个家仆跟他一起去爬山的,然后碰到需要披荆斩棘的时候,他的家仆会在前面做这些事情。然后谢灵运自己下不来山的时候,他会在山上痛哭,下面的县令派人去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把他坠下来。他不写这些东西。
这就是晋人的山泽游和林野娱。可是陶渊明说,我已经远离这些东西很久了,我现在去自然,我是“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陶渊明为什么要放弃山泽游和林野娱?我想用米兰·昆德拉的一个观念来解释。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面,他说:“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媚俗”这个词它有很多的翻译,现在的译者觉得它翻得不够好,觉得我们现在用“媚雅”或者“自媚”,或者“刻奇”来翻译更好。刻奇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一种低劣的模仿的感动,一种并不真实的存在体验,一种表演性的自我感动。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陶渊明觉得他愿意去面对自然,愿意去获取一种更加真实的体验。因此文人眼中的“山泽游”和“林野娱”到了陶渊明这里就变成了“披荆榛”和“步荒墟”。所以陶渊明是用一种农人的眼光在看待自然,自然是士人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而在农人眼中就只是“劬劳功烈”。
《抵挡太平洋的堤岸》
杜拉斯有一本小说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岸》。她说一些法国的穷人,他们移民到印度支那,然后想要在印度支那的海边种植水稻。可是旁边是太平洋。太平洋会有波浪冲毁他们的稻田,所以他们很努力地想要去建设那些堤坝,用堤坝来抵挡太平洋。可是你用堤坝抵挡太平洋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类的工作一次一次地被自然毁灭,然后稻田一次一次地被冲毁,人们在这之中面对的是死亡和绝望。
而陶渊明他所面对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因此当他带着子侄辈,在荒墟中间自己去拨开那些荆榛的时候,他在荒墟的深处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地方是丘垄。丘垄是什么?丘垄就是墓地。但是丘垄是没有墓碑的墓地。只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墓地,所以那个地不平,它是高高低低的,所以你知道那是墓地。
“徘徊丘垄间”,陶渊明发现这个地方好像以前曾经有人居住。所以他再仔细地去看,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些遗留下来的水井,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炉灶,以及有一些以前的人们在这里种植的桑树和竹子。只不过它们因为长久没有人管理,现在都已经腐朽了。
所以在这里有一种很让人觉得恐惧的感觉。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曾经在这个地方种植树木,都是希望能够做一个长久的计划。但是所有的树木还存在,可是人类的村庄已经不存在了。所以陶渊明就只能够“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说,他说陶渊明想知道曾经生活在这儿的人都哪里去了,可是他没有人可以问。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太荒了,他唯一能够碰到的人就是深山里面的采薪者,而这个采薪者告诉他的是“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死没无复余”是一重又一重地强调,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彻底地死了,他们一个人都没有留下来。我那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这里,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天才的联想。他说陶渊明为什么要在“死没无复余”的前面讲到这个地方“井灶有遗处”?他说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的生活不是建功立业,不是改朝换代,也不是什么山盟海誓,他的生活就是最普通的衣食,这种柴米油盐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可是哪怕你对于生活的要求这么低,你也没有办法苟全性命于乱世之中。
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忽然间被他打动了。我没有过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所以我对鲁迅的《社戏》里面的石马、石羊的感觉甚至比“井灶有遗处”的感觉更强,但是他把我们的感觉带到了更加普遍的一种个人生活的境遇之中。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陶渊明走到了比我们很多现代读者更不“刻奇”的那样一个层面上。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古代文学,会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士人他们都会假想,我的人生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有太多的文化,是因为我有太多的担当。这种观念就是著名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可是如果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世人本身的痛苦上,你的诗歌就会走向对于个人的命运不济的感慨。但是如果你发现不像你一样有文化,不像你一样有担当,甚至不像你一样关心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只关心柴米油盐,可是最后他们也是变成一片荒墟。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痛苦是普遍性的,就有可能走向对于生命本身的思考。而陶渊明就越过了对于很多文人来说越不过的障碍,走向了对于生命本身的思考。
因此就进入了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叫做“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一世异朝市”是什么意思?古代的人以30年为一世。所以在陶渊明和他之前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俗语,就是说30年这个世界就要变换一次。
陶渊明说我经历了这些事情,我才知道这样的话不是瞎说的,这是真实的。何况陶渊明在一生经过了那么多次的改朝换代,“一世所异”的还不仅仅是朝市,“一世所异”的甚至是一代。所以这是陶渊明不但观察历史,而且是他亲身经历历史之后得出的感慨。
世界如此,人生又如何呢?人生就是“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人生似幻化”,我们《金刚经》里面说“如梦幻泡影”,梦有醒的一天,幻想有结束的一天,水泡有破灭的一天,影子有消逝的一天。这就是人生的结局。
对于死亡的叙写
其实跟年轻人讲陶渊明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你如果把陶渊明的诗集打开,你就会发现,他差不多以两三首一次的速度、一次的频率在讲死亡的事情。
他在中年的时候就给自己拟好了死后的挽歌词《拟挽歌辞》,有三首。在第一首里面他讲自己将死之时,他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吃吃喝喝,可是今天怎么就已经阴阳两隔了呢?
《拟挽歌辞》的第二首讲自己死去,人们开始在他身边哭泣的时候,他说是“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假想自己方死之时的景象。
等到真的去送葬了,当我们被埋到墓穴之中,那些曾经来和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人,他们就“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好,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太残忍,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翻,陶渊明就告诉你说:你不要觉得它太残忍,因为它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他又在《形影神》这首诗里面说:“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我们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你现在看到他,刚刚还看到他在呢,下一个瞬间你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而且他有可能永远不回来了。
有时候很年轻的人他们会说,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诗?我还有大量的青春,这个诗我可以到中年再读。结果你往后翻几页,陶渊明又跟你说,“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陶渊明都给你已经想到了。
所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首一首地讲陶渊明这样的诗,最后学生们感慨说,陶渊明对于死亡实在是太客观、冷静、彻底,而且是太勇敢了。
陶渊明对于死亡的叙写,在中国古代诗人里面是非常特殊的。它的特殊性在于:第一,陶渊明比任何人都更加集中地写作死亡;第二,我们看魏晋之际有很多写死亡的诗,可是大多数作品都是把注意力放在对于外在的死亡原因的谴责上,比如说瘟疫,比如说战争。可是陶渊明写的时候,他不太在意这些外在的原因,他在意的是人必将死去的实质。
还有第三个,就是陶渊明对于死亡的叙写是非常不文人化的。我们看,面对死亡,中国古代的文人有他们自己的防御方式,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司马迁说,我死不要紧,但是重要的是我要写完《史记》,这样就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死一万次也不要紧,岂有悔哉!”曹丕也说“年寿有时而尽”,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文章是无穷的。
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假想,就是我如果得了道,或者说我有足够好的作品,死亡就没有那么可怕。这样一种防御当然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有另外一种防御方式,就是生儿育女,把自己死后的生活建立在后代对于自己的忆念之上。
可是陶渊明他不是这样来看待死亡的。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诗人之中少有的。他拨开我们涂在死亡上面的油彩。不管那层油彩是文明还是“得道”,他都会去看有虫子从骷髅的眼睛里面爬出来的实质。
所以陶渊明在他的《形影神》第三首里面讲一种彻底的死亡,说:“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所以不管你在生前有多么伟大的功业,你有多么了不起的作品,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掩盖你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最后会去面临死亡这样的一个实质。
所以陶渊明笔下的死是一种彻底的死,它不是眠息,不是仙化,而是灭,而是尽。
就像他在一首诗里面写浮云,他说这个浮云是“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所以我们会看陶渊明他常常用同一套语言来写植物、人、云,可是它们讲的都是同样一种生命的本质。
03 重生与种植
有很多人讨论陶渊明的死亡观到底是哪一种,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还是佛家的,或者是天师道的?可是谁都不能够说服谁。我觉得原因是,第一流的作者他们当然会受到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们不会成为某一种思想的附庸。文学和思想的合作关系,就是文学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更多不能被某一种思想所规整化的这样的东西——以这样一种复杂性来促进思想的发展。
所以陶渊明对于死亡的思考,我们很难说他到底是属于哪一家。
陶渊明对于死亡的真正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最有名的那一句话“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还是“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当然很好,但那只是一个理想,而理想不是没有缝隙的,所以陶渊明写出了那么伟大的一句话,他还是常常会觉得我要重新思考一下死亡。
所以我觉得对于陶渊明的死亡观更有代表性的,其实还是这一句:“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它代表了陶渊明对于死亡的思考走到了尽头,然后他发现死亡是神秘的、不可知的。
当陶渊明思考死亡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就反倒折返回生命中间来,所以就开始了他的诗歌中间的另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重生和种植。
我们在陶渊明的文集中间随便找一首诗。我很喜欢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停云》
我在我的小书《诗人十四个》里面写过陶渊明的一首诗,就是《停云》。我说如果有一天地球要毁灭,我们只能有一首诗留给未来的外星人来看我们这个地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那就留《停云》好了。那是因为《停云》它不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地讲人和一个时代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停云》它是讲在我们这个曾经雨水丰沛的地球上,有四季的往来,在这样一种自然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经营方式,人们进行耕种,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经营方式之下,人们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情感模式和审美偏好。所以《停云》代表了这个地球在农业时代的所有的一切。
《山海经·其一》
我觉得《山海经·其一》也是一首这样的诗。我最喜欢里面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还有“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三句。
这三句它不需要讲解,它没有任何的历史背景。你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在,你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或者经历这样的景象,我们都会觉得它是美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发朋友圈,去除掉那些只属于我们现代生活的内容,剩下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这首诗中间的第一层优美的地方。
可是它还有第二层。第二层是哪里呢?我们前面说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常地黑暗,我们说陶渊明他沉浸在对于死亡的思考中间,他对于死亡穷思竭虑。可是我们看这首诗,里面哪里有什么黑暗,哪里有什么死亡,哪里有什么阴影。它留下的就是轻盈和喜悦,就是清澈和透明。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他可以去面对那种最严酷的问题,可是同时他又能够在某些时候与那些问题隔离,然后沉浸在一种纯粹的生活的喜悦之中。
当他这样的时候,就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阴影停留在他身上过。所以我们才会发现陶渊明他能够写出像小朋友一样的诗句:“今日天气佳。”
这首诗里面还有第三层美好的地方,就是他说“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这只是这首诗中间快乐的一部分,这首诗快乐的另一部分是“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周王传》
《周王传》就是《穆天子传》。《穆天子传》是讲的神话中间的穆天子他渡黄河、过太行、出雁门,经过祁连山和天山,最后去寻找西王母的故事。而山海图就是带有插图的《山海经》。
为什么这种季节的变化,以及对于《周王传》和《山海经》的阅读,可以给陶渊明带来那么大的快乐呢?那是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所经受的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小时代的一些具体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在这个小的历史周期之外,还有大的历史周期,不受一家一姓的影响,不受一时一地情况的左右。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种大尺度的时空观?才能够去放宽看待我们生活的视野呢?那你就需要沉浸到自然的节律中间去;你需要去阅读地球史,而不是一个小时代的历史;你需要去走进到神话的时空之中去。这些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尺度。所以当你进入到这种大的尺度中去,你就可以在一抬手一低手之间,在俯仰之间,进入到一种仿佛是登山临海、时空穿梭般的情境中间去,获得一种宇宙大乐。那么这个时候附着在你身上的时代和个人命运的那种具体的压力就会消散掉。
讲到这里,我忽然就想到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跑到印尼一个叫做乌布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有全世界的嬉皮士,他们汇集在那个地方,每天冥想、唱诵、跳舞,向椰子树播送爱,向宇宙播送大爱。我觉得他们每天都处于在那种“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宇宙大乐之中。
可是好像这样的一种宇宙大乐批量供应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在陶渊明的诗中间,那种偶有会意可能是一种更加有价值、更加真实的体验。
正因为当我阅读陶渊明的诗的时候,那些最让我觉得轻盈明亮,最让我觉得充满喜悦的那些灵光闪现的瞬间,全部都出现在陶渊明描写自然的时候。所以这使我觉得,应当重新来理解种植这件事在陶渊明诗歌中间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要讲回到《归园田居》。
《归园田居》
我们刚才不是说,《归园田居》我们要先看它的第四首,看那片土地是怎么样一个在乱世之中充满了尸骸、遍地是坟墓的这样的土地。而陶渊明要选择那样的土地来“开荒南野际”,把它变成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再反过来看《归园田居》的第二首和第三首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归园田居》的第二首和第三首是一种对称关系,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它们都是在讲种豆。为什么呢?
《归园田居》的第二首的最后一句,叫做“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看起来它可以是讲任何的植物,因为它们都会在秋冬之际的霜霰到来的时候零落。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它讲的是种豆?
因为这句诗是来源于阮籍的一句诗,阮籍说自己的命运是叫做“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藿叶就是豆叶。我们知道豆这种植物,你如果种一架扁豆,你种下去不要很多的时间,到夏天它就会长满满一架,开很漂亮的花,结很多的豆荚,很美。
可是到秋天到来的时候,它们比其他的植物都更早地凋落。而且凋落了的豆科植物它会变得非常地轻,风一吹它就变成尘土。所以阮籍说我的生命就是“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而陶渊明借用了阮籍的这句话的意思,才说我们是“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所以他也是在讲种豆。
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非常地有名。可是怎么来讲它?
戴建业老师讲,陶渊明种的是个什么鬼田,“草盛豆苗稀”,要是我种田种得这个样子,我绝不写这个诗。戴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淘气。另外有一种说法,我们会看到有些人说,陶渊明写这首诗是讲官场太腐败、太黑暗,我要和他们对抗,所以我回去种地,虽然种地对于我来说很辛苦,但是我宁可接受这个辛苦。
可是我们真的去看这首诗的时候,你们觉得这首诗里面有任何的对抗的意思和任何的吐槽的意思吗?完全没有,对不对?所以这首诗里面有什么?
我们用讲另一首诗的两句话来讲它。《诗经》中有一首叫做《芣苢》,是讲春天的时候妇女们在田野上采摘野菜。元代的吴师道就说《诗经》的《芣苢》是“此诗终篇言乐,不出一‘乐’字,读之自见意思”。
那这个“乐”到底是什么?所有读诗的人都知道,它不是讲一种功利性的收获之乐,而是讲当我们沉浸在春天的原野上的时候,被春天的原野上的天气、被它新生的生命、被我们通过采摘和这些植物中间产生的关系、被这种东西打动而产生的一种快乐。所以它是一种非功利性的审美性的快乐。
我们把这首诗中间的“此诗终篇言乐,不出一‘乐’字,读之自见意思”,和王夫之说的“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把它拿过来讲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的第三首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归园田居》的第三首,它讲的其实就是沉浸在一个自然会生长得欣欣向荣的自然界中间,与日出日落一同作息,感受自然的繁茂,而且并不去考虑繁茂的到底是草还是豆苗。它讲的是一种这样的乐趣。
包括最后一句,叫做“衣沾不足惜”。我觉得这一句也很有意思。因为通过露水把衣服打湿这样一个事件,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混淆了自然和人的界限的感觉。自然通过这种方式把一自然的生命力多多少少带到了这个人的身上,人有一种“我成为自然一体”的这样的感觉。
正是在这种自然的力量的影响之下,陶渊明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存在感的话,就是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
顾随先生讲这一首讲得非常好,他说:“渊明‘种豆’一事,象征整个人生所有的事,所有的人,所有一生的事。”所以顾随先生不说这个就是种粮食的事情,也不说这个只是追求理想的事情,他讲这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事情。
因此在《归园田居》的第三首里面,它其实讲的是你在自然之中感受到的那种生命的节律、生命的顽强、生命的不可控制和生命的丰富的乐趣。
我前面说《归园田居》的第二首和第三首是一个对称关系。它们是怎么样对称的,除了都是在讲种豆子?
我们会发现,第三首它是往“灭”的那个方向写的。所以第三首讲的是说自然中间的所有植物,你在它身上倾注的所有努力,它有一种走向凋落的可能,它会凋落、会消逝、会被遗忘。可是第三首往另一个方向写说,它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就是它走向生长、走向发展、走向繁茂。人生可能就是在生和灭的二者之间,你去选择你往哪一个方向努一点力。在一个很小的可能性上,赋予一些掌握生命的这样一种可能。
大家最熟悉的《归园田居》的第一首,其实就是建立在第四首对于死亡的思考,在第二首、第三首讲生灭之间的辩证的基础上,它才去讲我为什么要“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绝不仅仅是说我要种一点豆子给自己吃这么简单。
回到我们开始说的那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那么奇怪,他要带着他的子侄辈到坟地上面去春游?陶渊明对死亡的思考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我觉得陶渊明对于死亡的思考其实停留在了肉体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他否定了道家的得道成仙,也摒弃了佛家的转世轮回,怀疑儒家的三不朽。
所以他对死亡其实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可是陶渊明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当他对于死亡的思考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反倒回过来重新发现了人生的意义。
人世的幸福
魏晋时代,典型的人生观念是“人生如流”和“人生如寄”。不管是“人生如流”,还是“人生如寄”,它都是把人生看做是命运大潮中间的落花败蕊;时代要带你往哪里走,人生要带你往哪里走,你就只能往哪里走。
可是陶渊明他所建立的一种人生观念,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给它命一个名,叫做“人生如植”,就是把我们的人生当作一棵植物,然后浇灌它,去欣赏它那个既可能繁荣、也可能不那么繁荣的“草盛豆苗稀”的结果。
陶渊明当然知道我们的未来就是“零落同草莽”,但是在凋落的一刻到来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去种植自己。那如何种植呢?
其实表现在陶渊明的现世追求中间,就是他的道德选择、他的政治判断和他的人际关系的建设。所有这些内容写在他另外三组很重要的作品里面,就是《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二首》。大家可以去看叶嘉莹先生的书《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她就比较多地把重点放在陶渊明的道德建设和政治追求这个角度的阐发上。
陶渊明是一个失败的农夫。可是我觉得他那个“草盛豆苗稀”的种植,其实和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并没有任何区别。
加缪说他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他认为西西弗斯通过推石头上山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主管了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陶渊明借由他的种植,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且对于陶渊明的幸福,我们甚至不需要动用揣测,我们只需要去翻开陶渊明的诗集,就会在里面一遍又一遍地找到他幸福的痕迹。
- 作者:FXY
- 链接:https://www.xpy.me/article/poet
- 声明:本文采用 CC BY-NC-SA 4.0 许可协议,转载请注明出处。